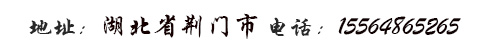写作的人总会保有一种天真
|
73烟纸店 故事本该 英勇且美好 Story 最好的爱情小说大约都是和信念有关的, 这个信念也不见得是一生一世、 无时不刻的永结同心, 但这个信念是和“抬头”的渴望与意志有关。 信念没法战胜贫穷、疾病, 有时也没法战胜诱惑。 但是没有信念, 有质量的爱就不会作为廉价的恩赐降临。 ━━━━━━ 《纸牌屋》里克莱尔的情夫汤姆在被这对极品夫妇抛弃之后,有一次重返白宫要和克莱尔聊聊,克莱尔问,“那你为什么想见我?”汤姆说,“我需要个结尾,我有个还凑活的结尾,但我不喜欢。”虽然一开始是安德伍德自负地提议,“有水平的作家都不会拒绝好故事”,可惜他还是低估了作家对于“结尾”的狂热。政治人物觉得汤姆是个词汇量很大、但并不需要任何“结尾”的次要人物。汤姆却执着地追求一个ending,为此还赔上了生命。这很有趣,给我很大启发。 写作的人总会保有一种天真,认为这个世界是可以通过语言命名和理解的。我们该如何运用现代语言在较短的篇幅里描述清楚对于世界、对于人生的不满足,我们要如何界定虚构与非虚构,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去年的梦境剪裁入今年的某个雨天的午后,这种剪裁算不算是一种虚构,而在此虚构与非虚构的壁垒之下,各文体真正的势力范围的边界又在哪里呢?我想了很久。我觉得这很像电影《夜行者》中走火入魔的路易斯,为了新闻效果,他重新编排了灾难现场。他也在修改,他濒入迷狂。 从简明的意义上来说,至少写小说可以让一些事情发生改变。写小说可以使一种物理规律被另一种物理规律破坏,可以令疾病恢复健康,可以起死回生,可以让有情人在街角的咖啡店再见上一面,可以让一切的遗憾召唤出挽回的契机。所以小说是需要“结尾”的,生活却不一定有结尾。 渴望讲故事的人,有了受辱、仇恨、心碎的经历,并不需要太大的词汇量,也不需要淬炼自己情感的质量,他只需要修改“ending”这一个意图,就能实现和征服世界差不多的欲望。“Whatif”建构的可能性无所不为。周星驰《大话西游》建构可能性、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机遇之歌》也建构可能性,没有一个人的人生会产生三种结果,但虚构可以。 散文却是一边写、一边探究,一边写、一边怀疑,一边写一边不断碰撞可写与不可写、写到与永远写不到的世界,探究不写到比写到更有价值的边界。不管我们多渺小,我们都是情景中人、历史中人。古往今来,它曾以无情的方式记下有情的事,也曾以有情的方式记下有头无尾的多少要紧事。离合悲欢,千丝千肠,在散文里永远没有挽回的可能性,这是散文的忍心。也是小说的不屈服。 假期里读闲书,我看了不少与爱尔兰有关的小说。众所周知,爱尔兰人非常会讲故事,经典如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是文学课上不可能绕开的名篇。近几年,我们翻译引进了不少爱尔兰作家的作品,其中有我非常喜欢的威廉·特雷弗,我还曾为特雷弗台湾版的短篇小说集《雨后》写作推荐序。 此外,爱尔兰小说家科尔姆·托宾曾来过上海,与王安忆教授对谈。谈到托宾的小说《长冬》时,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 《长冬》写的是一个年轻人在大雪覆盖的群山中,搜寻离家出走的酗酒母亲。在寒冷忧惧的等待中,他艰难度日,等待雪化后可能出现的母亲的尸体。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孤儿,孤儿没有父母,劝慰他说,好在这样的事你只会经历一次。王安忆说,“从感情上来讲,我觉得是真正有过丧亲之痛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可见,爱尔兰作家又是非常懂得生活的,懂得生死、懂得丧失、懂得真正的抚慰。 这场精彩的对话,其实还留有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尤其是关于多元文化背景之下作家的故乡情结。 托宾说,“你依然不能明白每一件事。我认为这一点上,中国人和爱尔兰人是有相似之处的。这个相似之处就在于爱尔兰人非常善于沉默,他们非常地迷人,也令人感到愉快。但是你永远不能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或许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遗产。我们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文化历史,我们曾经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当我去英国或者美国的时候,18、19世纪,当时爱尔兰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我们被邻居侵略。所以这么年的历史,在爱尔兰和英国这两个国家之间有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我认为这种困境一直萦绕在爱尔兰作家的头上。而且不仅仅是困境本身,还有如何从困境当中慢慢抬起头来。所以我认为中国作家也面临相似的问题,不仅是过去的困顿,还有如何从过去的困境当中抬起头来。” “从过去的困境当中抬起头来”,无外乎是“胳膊一再折在袖子里”的文学化的沉默。 我偶然读到美国华裔作家任璧莲小说《谁是爱尔兰人》,小说里写到“我以前总以为爱尔兰人和中国人一样,拼死拼活修铁路,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为啥中国人要比爱尔兰人强……”修铁路的爱尔兰人,《大西洋帝国》里也有。似乎在刻板印象中,住在布鲁克林的爱尔兰人男性从事修地铁的苦差事、女性则是做缝纫。这可能与大饥荒移民潮有关,年,土豆疫病致使爱尔兰陷入了饥荒,也谱写了一段残酷的历史。 但任璧莲小说里刻板印象的中国人比刻板印象的爱尔兰人强,电影《英伦对决》做到了。成龙扮演的关玉明是一个唐人街开餐厅的普通华裔,经历极其坎坷、接近全面不幸,因故卷入一场暴力争斗,为了复仇,他单挑IRA后胤及其降军贰臣。可见都是劳工阶层的苦难与传奇。仿佛在小说或影视剧中,爱尔兰人不是当劳工,就是当流氓,颇有些生活所迫的意味。今年也有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电影《爱尔兰人》会上映。 比起爱尔兰男性的艺术形象,在美国的爱尔兰裔女性形象也很有特点。托宾的《布鲁克林》当然是一例,说的是去美国消费社会见过世面的爱尔兰姑娘回乡之后心态不一样了的故事。爱尔兰姑娘的野心在《大西洋帝国》里也可见一斑,玛格丽特就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出身底层,通过自己的智慧挤入上流社会,最后甚至肩负起了一定的社会责任。 爱尔兰姑娘这种复杂的进取心,在别的作品中也可以见到。譬如我看了美国作家马修·托马斯的长篇小说《不属于我们的世纪》,说的是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在美国的故事。里面的爱尔兰男性是个知识分子,社区大学里教书,如果不是太太艾琳盯着他买房子,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诸如“我们已经来美国一百年了却没有自己的房子”这样的事。 艾琳在少女时期就很明确的知道,不能嫁给那个很有感染力的卡车司机。她会挑选生活搭档共同奋斗,热爱在劳动的基础上过上更好的生活,对生育问题很焦虑,热心为孩子比较学区房,喜欢计划分配经济生活……总之,和我们现在上海会看到的女性非常像。 当然,她也会失算,也会迷茫,她失算的部分就是她没想到丈夫在退休前就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这冲击了她一生的规划。她后来也出轨了,和玛格丽特一样,不知是不是一种偏见,《大西洋帝国》调停玛格丽特出轨行为的方式,是让她参与了妇女运动,这很像是一种戏剧上的平衡。 小说处理了一个棘手的处境,令人印象深刻:丈夫越来越成为日常世界的陌生人,钱不够用,她好像爱上了丈夫的俄罗斯护工,感恩节来临,她要如何向儿子解释爸爸去了疗养院而护工依然住在家里。我很喜欢她决定分手那天第一次坐在情人车里的动容,以及她相信结账柜员一眼就能看破他们关系的瞬间。 这的确让人相信,面对坚硬的疾病,面对难以修改的失败的命运,人忽明忽暗的内心就像月蚀,被脆弱狠狠咬掉了一些可以见人的光明,又终将复原。 我想最好的爱情小说大约都是和信念有关的,这个信念也不见得是一生一世、无时不刻的永结同心,但这个信念是和“抬头”的渴望与意志有关。小说里的爱尔兰女人怀有着这样的信念。信念没法战胜贫穷、疾病,有时也没法战胜诱惑。但是没有爱的信念,有质量的爱就不会作为廉价的恩赐降临。 好像小说里,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丈夫过世以后,妻子艾琳决定如果真的有来生,她希望自己能够被归入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标签类型里——某些标注着“假日”或“阳光”之类热情奔放的词条中。不过,这一辈子的她仍旧是她,永远不会再婚。 这个结局令人感觉到某种神秘的力量。来自于一对夫妇、一个移民家族“如何从过去的困境当中抬起头来”。这也是我最近浏览了不少于阿尔兹海默症有关的故事里,超越处理记忆与遗忘的历史辩证,走向了处理人与世界的交互关系。阿尔兹海默症的神经退行性病兆与新移民的文化认同面向达成了同构的隐喻:他这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扮演这个世界的陌生人——谁不是呢。 我没有去过爱尔兰。好在有文学,让我在心灵层面感觉到某种亲切。 ━━━━━ ※张怡微:青年作家。 性格不讨喜,人却挺好的。对时尚一窍不通,跟高跟鞋也装不了熟。对“鞋”第一次有了感动,是《岁月神偷》里说“鞋字半边難,亦有半边佳。一步难,一步佳。难一步,佳一步。” ※如果你也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给我们投稿。投稿信箱:yanzhidian 73hours.白颠的症状北京治疗白癜风的医院在哪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ingluna.com/yllg/3062.html
- 上一篇文章: 成龙受邀参加美国真人秀,观众这一举动可
- 下一篇文章: 高端观影继续发力IMAX中国九月票房创